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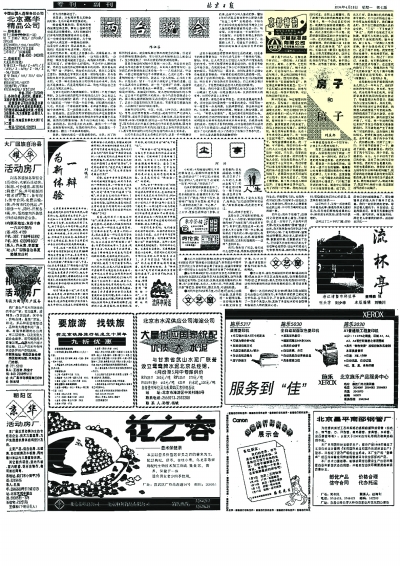
1994年4月18日见于《北京日报》副刊的《房子和稿子》,包含了刘庆邦对岁月和时代的思考。

2000年10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刘庆邦专访《“走红”是个贬义词》。
作家刘庆邦1994年4月18日发表在《北京日报》副刊的《房子和稿子》,呈现了房子与其写作的微妙关联,那里面饱含了岁月、时代这些宏大的主题。
从1972年到2019年,作家刘庆邦已在文坛耕耘47年。回望这47年,他的命运和时代紧密相连,他以坚韧和坚守,介入时代,反映时代,见证了风云变幻的社会变迁。他更前后花费30年,书写了深刻厚重的“煤炭现实”。
年轻时在“灯头如一粒小黄豆、摇摇欲坠”的煤油灯下走上写作之路,在煤矿当矿工时在床铺上写作,在自家厨房里每天闻着酱油味儿、醋味儿甚至煤油味儿写作……写作环境变了,但刘庆邦的初心未曾改变。
一篇压箱底的小说改变命运
“刚调来北京时,单位在建国门外灵通观分给我们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屋里除放下一张大床和一个衣柜,就没有放桌子的余地了。”在《房子和稿子》里,刘庆邦如此写道,这是1978年,彼时他写作正处于起航阶段。
1978年,是个神奇的年份。“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开始,知青大规模返乡,《新闻联播》从此登上荧屏。时代的变革波及河南一家煤矿的穷小子,刘庆邦和千千万万的同时代人一样,命运在那一年发生了转折。
刘庆邦1978年调进北京,之前他当过矿工,也当过宣传干事,一无大学学历,二无干部身份。正是因为一手好文字,被煤炭部看中,一家三口顺利进京,他也从此有了干部身份,还有了那处九平方米的小屋。
刘庆邦的第一篇作品是在煤矿单身职工宿舍的床上写的,最初只有一位读者,后来这位读者成了他的夫人。这篇小说写于1972年,年轻的刘庆邦心气儿高,不甘于命运的安排,突发奇想地想用小说来证明自己。而他写作的准备除了21年人生经验,还有就是铺盖卷里偷藏的好几本“毒草”,《红楼梦》《茅盾文集》等,那是他从学校图书馆偷偷抢救下来的。
当年全国文学刊物只有《解放军文艺》一家还在办,但它离一个矿工毕竟太过遥远。小说无处发表,刘庆邦只得将手稿放在了废炸药箱改的木板箱里,一放就是6年,等到重见天日时,纸张发黄,字迹模糊,只得重新誊抄一遍。
躺在箱子里的手稿于1976年迎来转机。国内文学刊物纷纷复刊,给刘庆邦带来巨大勇气,他将这篇名为《棉纱白生生》的短篇小说寄往《郑州文艺》,竟发在了头条。这篇压箱底的小说获得了30元稿费,那是刘庆邦一个月的工资,刘夫人欣喜之余做出决定,“这钱不能花,咱们存起来做个纪念。”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上世纪90年代,一批先锋派作家纷纷登上文坛,更明显的标志是,一辆自行车可以骑遍北京城,人和人之间没有隔阂,文学将人们拉得很近,文学杂志、文学人在那个年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作家刘恒在《北京文学》当编辑时,发现了刘庆邦发在河南文学杂志上的几篇小说,他写信向作者约稿,“把你的大旗移到北京来,用重炮向《北京文学》猛轰。”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刘庆邦珍藏至今。刘庆邦和刘恒的交往此后愈发密切,他回忆起,当年读了汪曾祺的《受戒》,惊喜地给刘恒打电话,刘恒回答说,“你喜欢读汪曾祺,也要读沈从文,他是汪曾祺的老师。”事实证明,沈从文的确对刘庆邦影响至深,“我对自然热爱,对人性美热爱,对人生热爱,感觉和沈从文很投合。”
1985年,刘庆邦写了短篇小说《走窑汉》,一个星期天,他骑着破自行车来到《北京文学》编辑部,“几千字的稿子,刘恒二话没说,立刻就看,看完马上就填发稿签。”刘恒眼光独具,《走窑汉》广受好评,《北京文学》主编林斤澜还郑重推荐给了汪曾祺。
不吹“萨克斯”,吹响“唢呐”
2012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第15版头条报道了首届林斤澜小说奖颁奖,刘庆邦获“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这个奖是对刘庆邦文学成就的褒奖,也是刘庆邦与林斤澜深厚文学情谊的美好纪念。
林斤澜有“短篇小说圣手”之美誉,他对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十分看重,任《北京文学》主编后第一位约的作家正是刘庆邦。“他说,你要接二连三给我写稿子,我们接二连三给你发。”文学人的相互承诺化为现实,刘庆邦计算了一下,他在《北京文学》发的作品有三四十篇之多,得过的《北京文学》奖多达11次。而林斤澜对他的评语,更成了永远的美好纪念,“过去短篇小说这条路上的车马很热闹,现在写短篇很寥落,庆邦是珍稀动物。”
那个年代浓郁的文学氛围,与文学人的无私提携分不开。刘庆邦的短篇小说《玉字》完成后,林斤澜毫不客气地提出修改意见,直言用力太分散,铺垫要更充分。他点拨道,不用面面俱到,就像去颐和园,不必所有景点都看一遍,到佛香阁等几个有代表性的地方就足矣。
“评论界有个说法,当代中国作家,谁要是不承认自己受过马尔克斯的影响,就是不诚实的。但对我而言,要是承认受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就是不诚实。”上世纪90年代前后,西方文学思潮席卷中国文坛,在这样的文学大潮前,刘庆邦的《百年孤独》阅读经验有些“孤单”,“我读了个开头就没再读了,不能说《百年孤独》不好,但我看大家都在学习,都在模仿,既然大家都在模仿,我就算了。”
上世纪90年代,国内文学作品曾一味追求幽默、诙谐,解构主义的作品多了,意识流的作品多了,躲避崇高回避崇高成为时尚。刘庆邦喜欢读茨威格的小说,他欣赏茨威格的心理分析,也曾跃跃欲试。但写作经历告诉他,心弦绷得太紧,心脏跳动太快,“我觉得不行,就放弃了。”
种种尝试过后,更坚定了刘庆邦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风格,如同林斤澜对他的评价,“不吹萨克斯,不吹法国调,吹响的是自己的唢呐”。在那个求新求变的年代,刘庆邦的选择无疑是特立独行。
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后,信息大爆炸时代到来,网络、新媒体、娱乐文化、二次元文化纷至沓来。作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是追赶潮流,还是坚守纯粹,选择和挑战摆在了作家们面前。
事实上,那个年代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很多作家转型成为影视编剧。刘庆邦比很多同行都更有在影视业发展的机会,《神木》发表于2000年《十月》杂志,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中篇小说之一,由《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也成为国内电影经典之作。但刘庆邦并未因此选择与影视亲密接触,“我想做纯粹的文学,写剧本就改变小说的文学品质了,很多作家做着做着编剧就回不来了。”
每个家庭都是“延伸”的矿井
1997年5月8日,《北京日报》刊发消息《全国煤炭文学乌金奖揭晓》,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家道》、短篇小说《屠妇老塘》获一等奖。不大的篇幅,记录了一段珍贵文学岁月。
从《断层》《红煤》到《黑白男女》,刘庆邦的“煤矿题材长篇小说三部曲”创作前后持续30余年,“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
刘庆邦1986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断层》,此时文学思潮潮起潮落,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你来我往。他回忆说,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他从改革的角度写矿上生活比较多。而主人公的确也有蒋子龙笔下经典人物“乔厂长”的影子在,作品诉说了人应该在工业文明过程中具有现代化意识,在今天仍有其独特价值。《断层》是在厨房的方凳上日积月累攒起来的。他立下规矩每天写3000字,早上4点至6点写作,然后再上班,历时3个月完成。《断层》最终挣了六七千元稿费。
世事沧桑,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到来,“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打工,成为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也无法回归乡村,而刘庆邦的《红煤》让人们深入了解了社会转型期农村青年进城打工的生存状态和深层情感心理。他记得,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很多矿工被困井下。他去采访时,在矿工俱乐部门口遇到一个等待父亲的小伙子,小伙子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话令刘庆邦震惊。“这孩子要参加工作,必须要以父亲的死亡为代价,这里面有深刻的生命悲哀。”这个细节触发了创作灵感,刘庆邦此后写成了《红煤》。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煤炭能源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矿难频发,煤矿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场域,刘庆邦用他的文学书写呈现了灾难,更挖掘了灾难背后细微的人性。“大事故如瓦斯爆炸,有几年连续发生,死亡上百人。瓦斯爆炸造成大规模人员死亡之后,矿工家属怎样向死而生,怎样建立新的平衡,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
“2015年出版的《黑白男女》是我挖了那么多年,终于挖到的大块优质煤炭。”刘庆邦说,写《黑白男女》是他由来已久的心愿,1996年产生想法,到写的时候已快20年过去了。他说,这次写作是还债,如果不还,会不得安宁。
那是1996年5月21日,平顶山一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84人死亡,时任《中国煤炭报》记者的刘庆邦次日赶到现场采访。矿工家属们的悲痛,让他的感情受到强烈冲击,他把目睹的细节写成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命悲悯》,很多矿工读后嚎啕大哭。此后,2004年至2005年,中国煤矿先后发生三起重大事故。先是2004年10月郑煤集团大平煤矿瓦斯爆炸,死亡148人。接着,11月陕西陈家山煤矿发生矿难,死亡166人。次年2月,辽宁阜新孙家湾矿难,死亡200多人。不到四个月时间,500多工人死于矿难。“我觉得我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要尽快把小说写出来。”
“这是我看重的小说,常常写得眼湿,这里面包含了我太多情感。”刘庆邦说,这部小说,他没有直接写遇难矿工,但家属就是矿工的“延伸”,每一个家庭都是“延伸”的矿井。为此,2013年那一年,刘庆邦走进河南大平煤矿,在13天时间里下井,与矿工同吃同住,走访遇难矿工家庭。
68岁的刘庆邦说:“现在好多娱乐化节目,一味搞笑,没有提升人们的审美趣味,反而降低了人的审美趣味。”他认为,作家有责任坚守高的审美趣味,文学是发掘美、表现美的,而他会坚守到底。





